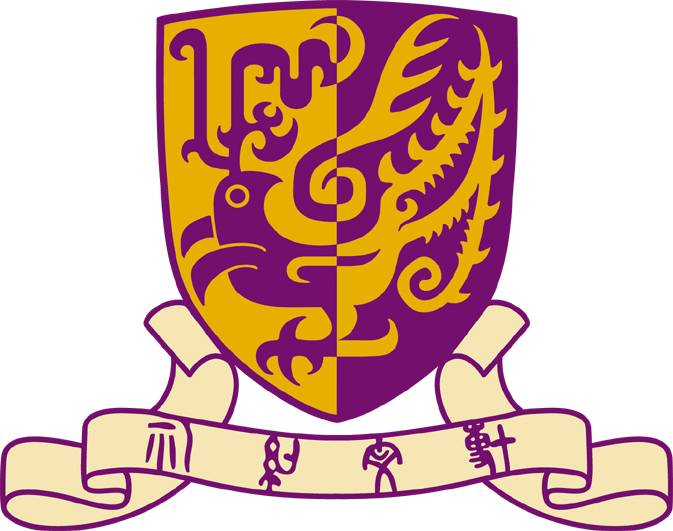卓嘉健對跨國網絡的研究,始於他的本科畢業習作。因緣際會、誤打誤撞之下,嘉健去了香港的印度錫克教廟,發現和在華人廟宇遇到的狀況大不相同。「之前在華人廟宇做過一些小型研究,那些廟祝或是廟宇委員會的成員,我可以用一個詞形容,就是很『香港』。一進去他們就會問你哪裡來、讀什麼專業,一聽到人類學,就會問,『即係乜嘢?搵唔搵到食?』我解釋了一大通,他們還是很質疑。面對我的提問,他們又會說,你問這麼多做什麼?這些都是沒有用的!」對比之下,錫克教廟給嘉健帶來了第一次「文化衝擊」:「當時很少華人會進入他們的社區,但我發現錫克教社群其實是非常開放的,很多人很熱情、開放地和你說很多故事。」在田野之中,嘉健發現這些印度人的網絡性很強,和家鄉仍然有很強的聯繫。對於社會當中的少數族裔來說,跨國聯繫有何意義呢?這成為了卓嘉健的人類學探索中的核心命題。

「人類學往往要求研究者自己親身去發掘一個研究問題出來,這個研究問題必須是burning from inside的,不可以是一個given。」從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畢業以後,卓嘉健遠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。「我的指導老師是項飆教授,他有一種對研究的執迷和執著,和對所研究的社群的透徹的親密性。對每一個問題,他首先就會問,為什麼我會對這個問題感興趣?這個問題的現實重要性是什麼?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,可以對認識世界有什麼新的貢獻?」嘉健的博士研究田野點是浙江省紹興市,當前中國最大的國際布料出口貿易區之一。「一開始我的研究問題是很不清晰的,可能只是想追踪印度人的移民網絡,以及考察他們的身份認同。這些問題,用項飆老師的話來說,『好假』。這可能是學術界看待ethnicity的視角,但好多時當你帶著這些理論框架進入田野的時候,會發覺當地人原來don’t care about it at all。」嘉健笑言,在進入田野之後,他原來構想的研究問題完全被打碎,一切從零開始。

「一開始當然因為毫無方向走了很多冤枉路,但在當地生活一段時間之後,自然而然地,慢慢你就會發現一些大家共同關心的、最為重要的問題。」紹興是一個小城市,但經濟往來極為全球化,有許多來自南亞、中東、東歐和非洲的商人在此進行中間貿易,賺取差額和提成。「用Gordon Mathews教授的術語來說,這些都是low end globalization。有趣的是,我發現這些商人之間的合作關係是很奇妙的,在這些低端的貿易活動中有很多爭吵和爭執:產品質量不達標、不按照合同要求、付款不準時……整個貿易鏈的牽涉面很大,每一個環節都可能出問題;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,簡直亂七八糟。但問題正正就是,為什麼這麼混亂的經濟體系可以維持下去?從金融風暴、匯率升跌到貨幣管制,種種外圍的不穩定因素,對地方經濟都有不同程度的打擊,但後者的基本生命力始終是常在的、可以維持下去的。」
嘉健認為,這難以用經濟學理論簡單解釋,而需要用民族誌的方法,挖掘這些中間商尋找生存空間的策略、觀察他們之間微妙的網絡性。「譬如說,有些中國廠家把貨物發過去之後,印度的中間商一直都不給錢,但他們還是可以合作十幾年,原因是什麼呢?我發現其中有兩個重要因素:其一,這些印度商人的網絡都是一層判一層的,資金網絡很複雜。但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下金融中心:杜拜。從信用、合同安排,到和正式金融體系的混合,在杜拜都非常成熟。在浙江的印度人,大部分都有很濃厚的中東背景。在由朋友、親戚、非正式和正式銀行的複雜網絡支持下,這些印度人的資金調動能力是很強的。中國人不是對這個人有信心,而是對他們背後的網絡性有信心,所以才繼續和他們做生意。其二,在中國政府有一個退稅政策,很多中國人和印度人會在紹興合謀,爭取更多的退稅利益。」

在人類學的視角之中,這些經濟活動的意義,並不止於經濟層面。卓嘉健直言,「很多時候,你不能怪這些人在日常的經濟活動之中偷呃拐騙。」他分析說,這些行業在全球經濟體系之中,是很邊緣和底層的,他們也難以逆轉這種系統性的不公平。「老實說,他們不會有任何方法可以擴大他們生意的規模,令到他們可以和Zara,H&M這些大型成衣零售企業對抗。中間商的角色是幫客戶爭取一個最好的價錢,在資本鏈條中榨取剩餘價值。」儘管如此,嘉健卻認為,這些中間商看似混亂的合作關係,是有雙面性的。「他們既維持一種不公平性,但同時亦在擴展本地經濟體系的生存空間。當你身處一個不公平的經濟結構之中的時候,你如何運用社會網絡、流動性和個人冒險,來最大化自己的生存空間?這些在普通人看來可能morally questionable的商業行為,其實是有很強烈的moral implication的。」在嘉健看來,對這群在全球化浪潮之中並不矚目的人的考察,或許能幫助我們發現一些新的詞彙、新的故事,來理解與挑戰權力結構。

從香港、牛津、紹興、萊頓到上海,在十多年的人類學歷程之中,卓嘉健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;這段旅程,原來發端於嘉健對香港本土人類學的關懷。「環顧香港學界,本土的人類學家其實不多。我所說的本土是,從小在香港長大成人,我認為,周圍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是很大的,而這種來自地方的親密性,正正是人類學的生命源泉。這也是為什麼我希望繼續進修,以後回到香港——不一定是要physically回到香港,而是想建立一個從香港本土的經驗出發的、獨特的人類學視角。」
香港近年來的社會與政治形勢,或許令不少人感到悲觀。卓嘉健卻覺得,這對於香港本土人類學來說,可能是一個歷史性契機。「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我們第一次以『邊緣性』來認識國家主義和全球化。以前我們以為香港是世界的中心,這個sense在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還是很強的;但現在,大家可能反而會用被邊緣化的、被剝削的視角來看香港。」而邊緣性,在人類學理論當中是很有生命力的。批判很多時候來自邊緣——身處邊緣的人,觀察世界有一個不同的視角。「無論你是在中國一個小鎮的印度商人,或是現在受到國家主義、資本主義、官僚主義壓迫的香港社會,或是在大學一個資源緊拙的學系裡的年青學者,結構壓迫令你喘不過氣、社會現實令你生活很不穩定,這看似難以改變。但是從學術的角度看,很多時候,如果要推動社會改變,必須有新的知識生產,來更新對社會的理解,進而發展出感染力更強的社會批判。」卓嘉健說,「十年前,我很想以香港的本土人類學來參與世界人類學的辯論,到了近年、香港的社會政治形勢改變了的時候,我的想法沒有改變,甚至覺得現在恰恰可能是一個機會。我想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,香港可以參與到一個邊緣性的、批判全球學術理論的陣營之中。香港人類學家可以對世界人類學理論作出哪些貢獻與批判,我們能夠做到什麼程度呢?我覺得這是值得年輕一輩人類學者努力和思考的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