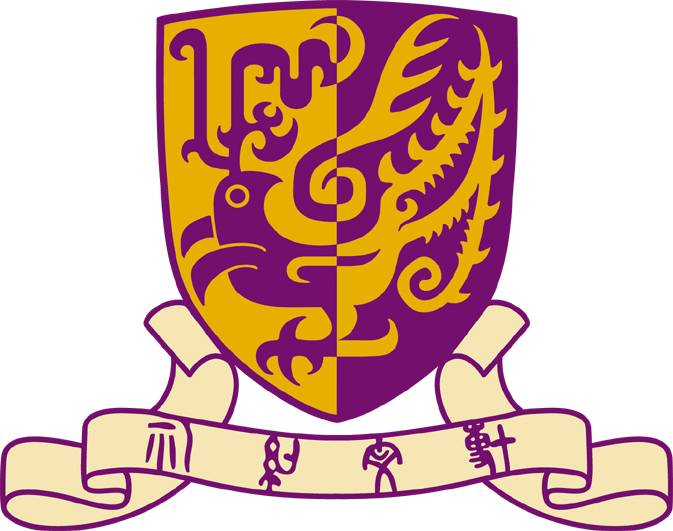「那時候我發現,沒什麼學術文獻是關於香港的lesbian的。看看外國,尤其是歐美,九十年代是很蓬勃的時期——那時候還未叫做LGBT,是稱作Gay Studies——但香港真的近乎沒有。」2000年初,Franco由社會學系畢業,繼續於中文大學升讀性別研究(人類學)碩士,決心把握機會,研究香港的女同性戀社群。「現在回看,當初膽粗粗地嘗試,論文未必寫得很好,但的確是留下了一個有其意義的記錄。」
在田野調查之中,Franco發現,困難不在於尋找受訪者,反而在於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、與受訪者的關係。「你既是她們中的一份子,又是一個人類學家、研究者。和她們相處的時候,你有時是需要分清楚現在是hang out還是做研究。所以真的坐下來做interview的時候,我都要會清楚地告訴受訪者,『我即將要寫一份論文,這個訪問是為論文收集資料,是自願性的,你可以拒絕。』而到落筆寫的時候,她既是我的朋友,又是我的研究對象,要提醒自己好好拿捏,如何較為客觀地描述我的發現。」Franco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在香港的印尼移工,這個問題更加凸顯。「印尼移工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社群。博士生有很長的時間可以進行田野調查,當時,我當然是日日都想和她們聯絡、每個禮拜都跟著她們參加活動。很理想地,因為我和她們成為了好朋友,所以她們會展現很真的一面給我看,讓我能瞭解她們是怎樣的人、如何理解她們的同性關係。但到我寫完論文、博士畢業,工作又開始忙碌的時候,有時她們來約我,我只能推辭。那麼,我和她們的關係是否『功成身退』、『用完即棄』呢?」如何處理與平衡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雙方的期望,是人類學方法論常常討論的問題。
說到印尼移工的同性親密關係,大家常常會問「為什麼(why)」:為什麼她們會變成了同性戀?是不是因為在香港的生活太寂寞,或是有這樣那樣的特別原因?Franco卻表示,她的研究不是要回答「為什麼(why)」,而是關於「怎麼樣(how)」的。「她們自身怎樣去理解自己的這個轉變,是重要的。當然,坊間可能覺得這個研究角度很悶、不夠爆,但其實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。」Franco發現,印尼移工社群的恐同情緒較低,也較為容易表達對同性的興趣,使得她們感到同性之間的親密關係也是有其價值,至少不會極為抗拒或被污名化。Franco亦觀察到,印尼移工社群的不少活動,都有女扮男裝的元素,甚至有專門為Tom boy而設的時裝表演。「我就覺得,誒,我們香港的女同性戀社群都還沒有做到這樣呢。」相較之下,印尼移工很擁抱這種女性男性化的表演。她們怎麼樣透過休息日的一些表演和活動,令到她們的同性關係變得有意義的,是有趣的研究課題。
「主流的想法是要有一個很清晰的劃分,『究竟佢地係咪lesbian啫?如果佢地以前鍾意過男人,冇理由係lesbian喔!』是一個很非黑即白的分類。所以很多人會覺得這些在香港的印尼女性是『假』的同性戀。但這種分類方法,其實並沒有真的代入到她們的處境、理解這段同性關係對於她們的意義何在。」Franco說,她的不少受訪者表示,如果回到印尼,有合適的男性對象,也可能會考慮結婚。「一般人就會覺得,『吓,咁即係點呀,咁亂嘅?』但人類學研究則會欣賞這種流動性,考察在不同的文化場景之中,人們如何為此時此地的生活創造意義。」
Franco赴美國修讀博士畢業後回港,現時於浸會大學任教。近年來學術界的競爭日趨激烈,然而Franco表示,對於後來的同學,如果個人和家庭條件允許,讀碩士、博士,做學術研究,絕對是一個值得好好把握的機會,她一定會鼓勵。「到現在我再回想,我都真的很珍惜我做田野調查的經驗。尤其是如果有機會到海外深造,那種體驗更加難得。當然,可能你的付出和金錢上的回報不成正比。但是看看統計數據,其實這不僅僅是學術界,而是全香港各行各業都面臨的問題。當整個社會變得更加不公平,不是只是清潔工才被剝削,而是所謂學者都處於一個被壓榨的狀態。但是不是就要說『你真係慘了,讀咁多書都係賺咁少錢』呢?我想這又會fall back into那種『讀更多書是為了賺更多錢』的意識形態。人類學學術研究的經驗,不是你的月薪可以給你、不是錢可以交換的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