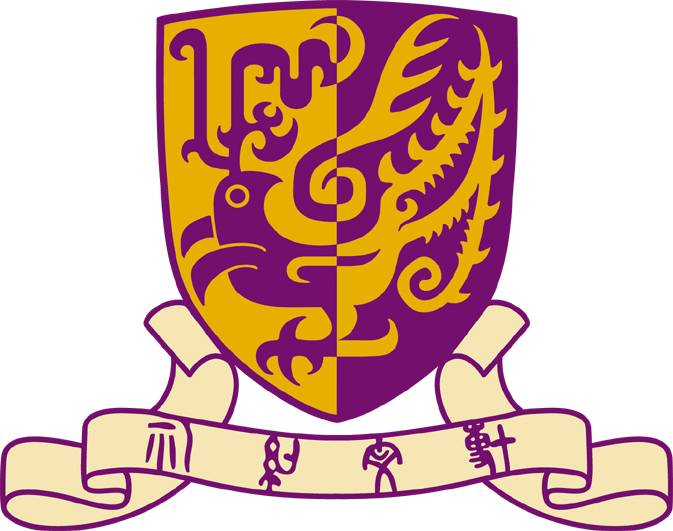「以前可能下課會用一兩個鐘和身旁的同學聊天,那時,變成online上完堂就立即換衣服出門,去找清潔工聊天。」Kiki的畢業習作(Final Year Project)之田野調查,在2020年暑期開始到2020年尾進行,研究疫情之中,清潔工人的處境和應對。
「一開始是在ANTH2020 World Ethnography上,讀到一本書,有關紐約的清潔工,令我開始想也了解一下香港的清潔工人的情況。和導師Wyman討論之後,他建議我可以把這個群體放在疫情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之中來研究,我就決定做這個題目。」Kiki本身認識兩位在屋苑從事清潔工作的朋友,想藉此機會認識他們更多;除此之外,她也選定了一個垃圾站作為研究田野,看看是否會有不同發現。
「我觀察到的共同之處是,面對疫情,屋苑和垃圾站這兩個群體的清潔工人,都會更多地嘗試去build up他們的social circle。」Kiki發現,疫情之前,同一個垃圾站的工友之間,未必有很多交流。「原來,他們的工作,很多時候是分配好給一人或兩人一組獨立完成。來到換了衫就開始工作,做完就走,比較少有機會讓他們互相認識。但疫情期間,大家一開始都不太確定要怎樣做,於是會更想建立同事之間的關係,有事情可以一起商量。例如他們覺得公司的指示不清楚或者缺乏相關物資的時候,就會問問同事,互相幫忙。慢慢平時交談也多了,彼此更熟悉起來。」
疫情當然亦為清潔工人帶來壓力。「大家摸什麼都要隔著張紙巾,又要丟棄口罩,垃圾一定是多了。有時路上有人走過都會說,『怎麼垃圾桶滿了都沒有人收?』。而在屋苑,清潔工常常收到投訴:有住戶覺得他們清潔得不夠;又有住戶說,清潔工這麼髒,怎麼常常在電梯裡出現。」清潔工們感到,似乎他們無論怎樣做都不夠好。Kiki說,垃圾站的清潔工們因此有一個「策略」:「他們特意在lunch time人們在街上的時間,去清理垃圾桶,『我就是要行出去做給他們看,不是我們偷懶啊,我們有做嘢的啊!』可以見到,清潔工人要負擔更多工作,同時還要表達、呈現出他們的確有在努力工作,避免成為被歸咎的對象。」
Kiki的另一發現和空間有關。Kiki介紹,屋苑裡沒有一個地方給清潔工人坐下來休息,原先他們會在屋苑的公共空間有檯凳的地方吃午餐,但是有疫情的時候,在外面除下口罩進食又會招人話柄。「這令到清潔工們開始想,『不如我們自己找個地方吧!』於是,他們在屋苑裡一個比較隱蔽的位置,set up了他們的space,放了檯凳、沙發、還有雪櫃,成為了一個工友們可以使用、休息的空間。你會看到他們很重視這個空間的運用,很細心地佈置,希望大家可以在這裡感覺舒適自在,而不是身處一個不愉快的工作環境。」
「我本身有一個hypothesis是,疫情之下,社會大眾會把很大的期望和責任放在清潔工人身上;另一方面,因為他們的工作屬性,清潔工人似乎是一個risk group,一定是面臨危險的一群。」在田野中,在和清潔工人的傾談和交往中,Kiki有不少驚訝的發現。「所以,我本身會擔心他們是不是會很大壓力、很不開心,但原來,其實他們自己很樂觀。有些清潔工友會說,『得喇,我做開清潔幾十年,我知道什麼是乾淨。』我也見到他們的衛生意識是很強,每做完一件事就會洗手,有時一邊和他們聊天,說十句話可能已經洗了五六次手。他們有經驗,有自己的一套保持清潔的方法。雖然也會有擔心,尤其是他們的家人朋友,有的會勸他們不要繼續做這份工作了,但他們自己對danger和risk的理解和判斷,可能有些不一樣。」Kiki發現,就算是在同一個地方工作的清潔工人,背景也可能很不同——年紀通常比較大的清潔工們,有些是為了經濟因素、維持生計必須繼續工作,有的卻覺得這是「嘆世界」——「有一位清潔工友,在這一區有很多朋友,每一次收垃圾,其實他是enjoy的喔,不覺得辛苦,因為他一行過去,街坊們都認得他、和他打招呼,他反而覺得這樣工作是一種享受。」
「好有趣,你每一日落field site,都會覺得有些新的東西,或者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會出現。」說回自己,大學最後兩年的學習,受疫情影響而反複變動,Kiki說她很受清潔工受訪者們的啟發:「老師們好勁,很快可以轉到online mode,課堂上會設計不同的活動給大家參與,令同學不會覺得整天呆在熒幕前沒什麼精神。我自己的話,覺得疫情之下都是可以很努力地學習的,也會嘗試用一些方法令自己更投入——我想,這是受到清潔工朋友們的影響,在不確定性面前,學習他們積極應對的態度。」
【延伸閱讀】Hong Kong Sanitation Workers and Their Strategies under Uncertain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