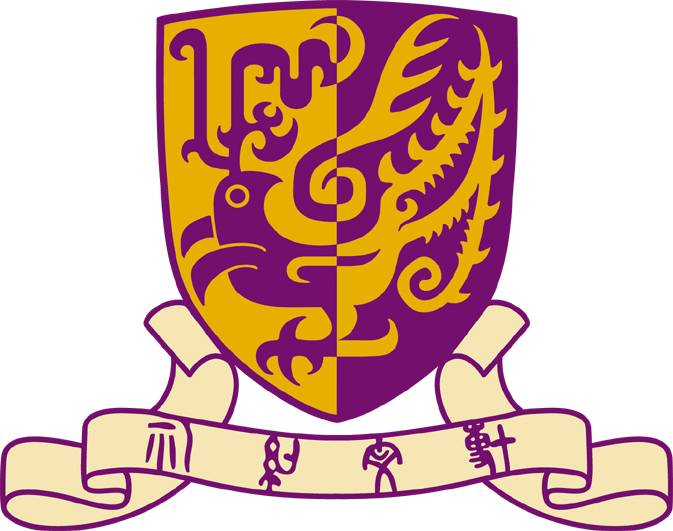Phoebe的碩士論文是關於香港的印尼家庭傭工的。她在研究當中發現,有些雇主對傭工有著對舊時的「妹仔」類似的看法,而僱傭公司在推銷印尼傭工時,經常把印尼女性「包裝」成鄉土、淳樸、思想單純而保守的,以迎合雇主對於模範傭工的想像。但把這個框架套在現時的僱傭關係上,其實是不work的;很多雇主的工作和家庭狀況令到他們不得不聘請外傭,但其實自己也捉襟見肘,在狹小的居住空間中很難為傭工提供良好的住宿和工作待遇。外傭所受到的不合理對待乃至欺壓,既源自文化上的誤解,也有制度性的問題。然而,Phoebe坦言,她當時選擇做這個題目,主要是出於研究目的,並沒有特別帶著想要解決社會問題的心態。「我不是那種在中學、大學就很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的人。雖然一直都關心、也都有個問號在腦海之中,但那時的我缺乏行動的動力,也好像找不到一個適合自己個性的參與方法。」
畢業之後, Phoebe的論文的外部評審教授找到了她,邀請她擔任一個印尼女性賦權項目的研究統籌。「我和許多當地的婦女組織合作,一起去進行一些研究項目。一方面,很多小型機構在制定綱領的時候,都是憑著經驗或直覺,覺得這件事是不對的、是需要改進的,就去做了。但當他們要和政府打交道或是面向大眾宣傳的時候,就缺乏很實質的數據和資料去支持他們的訴求。另一方面,有時社運人士和受眾之間的關係也很微妙,社運組織很需要了解他們服務的群體的想法和需要,使他們得以參與進來,發揮主動作用。我當時做的行動研究(action research),就是在這兩方面為公益組織提供支持。」人類學的學習使Phoebe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技能。「我面對的議題可能是比較技術性的,例如關於經濟、勞工政策、土地權益等,但研究方法都是共通的。人類學也令我的眼光更加開闊,會看到印尼的、泰國的、孟加拉的女性與工人,或者以前香港的製衣女工,或許在文化上和面對的環境有所不同,但事實上、在當今世界緊密聯繫的政治經濟結構之下,他們都受到許多共同作用力量的影響。」Phoebe說,這些研究,或許未必如學術研究嚴謹、未必有高深的理論,但在實際的社會行動之中是有它的用處的。
Phoebe在當時的工作中接觸到很多來自印尼以及世界各地的社運人士。「受金融海嘯直接衝擊後的印尼百廢待興,可獲得的資源很少,而做NGO的朋友,他們的生活水平也是很基本的,沒有什麼物質享受。再加上,從印尼結束獨裁統治到我在那裡工作的時期之間,不過十年光景。一個蓬勃的公民社會已經在發展之中,但是長期不自由的社會環境和教育制度的影響仍然很大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,這些社運人士全都是很能言善辯的,但是做研究的話,需要前文後理、條分縷析,而這樣去寫作對於他們來說就很困難。我覺得很奇怪,明明他們說話的時候都雄辯滔滔,怎麼一到要寫就不行了呢?有一次,他們就和我講,『Phoebe啊,你知不知道,要是在以前我都我手寫我心的話,現在你就看不見我啦!』他們解釋說,在以前,他們是很少有批判思考和寫作上的訓練,而且白紙黑字的東西,很容易變成罪證。」和這些社運人士的交往,對Phoebe的衝擊很大。親身體會到他們如何在艱難的處境下不懈努力,為社會正義而奮鬥,使得Phoebe也更有熱誠投身於這個領域當中。

「人類學常常講文化相對主義,而我在NGO做人權方面的工作的時候,則很強調普世性、強調人權理應是普世價值。這個關係要怎樣處理呢?」Phoebe指出,「文化」這個概念,有時容易被有權有勢的在位者濫用,以「歷史傳統」和「民族特性」為由,抗拒「外來勢力」的影響。「但其實想深一層,人類學之所以要叫『人類』學,正正是在說人類是同一個物種,有一些基本特質是共同擁有的。人類學要問的是『人何以為人(what makes human human)』,這也是我在工作中經常遭遇、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。」Phoebe進一步說,人類學的學習也讓人清楚地認識到,從古至今,文化都是不停流轉和變化、無法絕對地分割開的。「除了研究方法的學習之外,人類學的訓練也幫助我建立了世界觀、價值觀,讓我明白,看事情的方式和角度是可以有所不同的,但在差異之中又可以找到共通之處。這是人類學教給我、而我終身受用的東西。」
當今世界似乎越來越兩極化,無論是階級、種族、宗教還是社會生活的其他面向,都好像越來越沒有相互共存的餘地,而是要分出高下對錯,非黑即白、壁壘分明。Phoebe覺得,正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中,人類學的研究與態度,更加必要而彌足珍貴。「人類學著眼文化差異,但並不是要區隔不同的群體,而是期望在認識社會文化差異的基礎上,溝通、理解,相互尊重,共同生活。人類學家關注的或許是邊緣的社群、討論的似乎是小眾的話題,然而正正是這個取向,可以提供一些洞見,是現時社會所缺乏的。人類學的研究,如果能和社會發生真正的對話,會是很好的事情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