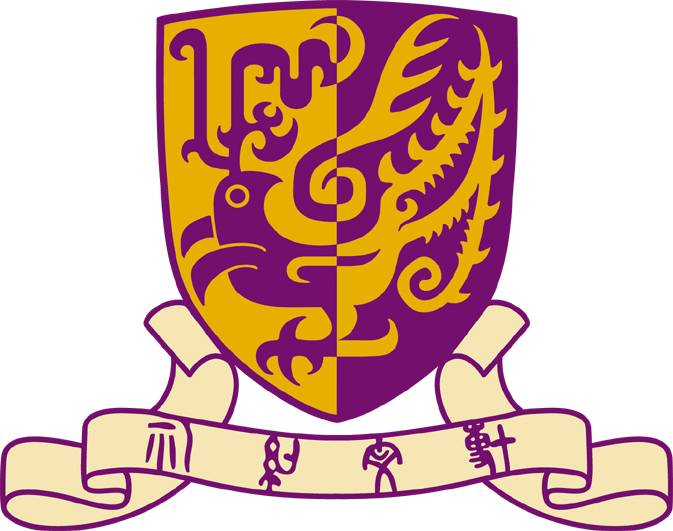不少NGO項目著重於扶貧和經濟發展,看似理所應當,卻讓Rebecca生出越來越多的疑問。「我之前在大陸的農村地區做社區發展工作。做著做著,發現村民內部有不同分層,一些項目因為要求參加者有一定的種養經驗或配套款,可能比較有利於中層或社區中的能人,對基層的村民卻沒什麼幫助。我又會想,其實當地的村民是否真的需要我們的『幫助』呢?作為外來者,我們是否真的能理解當地人的需要呢?我們是滿足村民的需要,還是我們自己想幫人的需要?」朋友介紹之下,Rebecca決定休整一下, 修讀人類學MA課程。
「平時,我們是假設農村社區是需要『發展』的。人類學卻教人反省,為什麼要發展、什麼叫發展呢?」在學習過程中, Rebecca對之前工作中有所疑慮的地方有了更深入的思考。「認識了什麼是資本主義、認清了資本主義怎樣影響生活中的每個環節。例如說,我們會期望村民要發展、過像城市人一樣的生活,但其實當生活狀態因外力而改變時,他們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也會連帶起變化,有可能因外來資源的投入而引起競爭,甚至社區關係破裂。這些未必完全都是好的、進步的事情。」
畢業後,Rebecca入職一間較為另類的NGO「社區伙伴」,著力於人與人的關係、人與自然的關係的重新構建。但她始終覺得還不足夠。「我們在推廣一種另類的、可持續的生活方式,都是鼓勵別人做、在旁邊看著別人做……其實自己都唔知work唔work嘅!要是你真的相信那件事的話,為什麼不自己親身實際去做呢?於是我就辭了職,希望可以從事前線的農業工作。」
Rebecca認為,推廣可持續的生活方式,是一場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:只要每個人都改變她的生活狀態和生活習慣,最後可以改變社會。「但在實踐的過程中發現其實很難的……資本主義的文化及其邏輯已滲透在我們生活的各方面:大家看重物質,講求競爭與資本積累,將原子化的家庭為理所當然。社會大眾的觀念與我們所倡導的價值南轅北轍,要推動改變實在困難。」人類學讓人看到社會現存的問題,但卻沒有提供一個現成的解決辦法。加入社區伙伴,讓她看到社會改變的可能性,但現實實踐又讓她再度懷疑這個可能性。雖然如此,在台灣聽到的賴青松先生的分享,鼓舞了Rebecca。「資本主義的巨輪已經太大,但青松提醒我一件事,是呀,世界可能改變不了,但還是可以在資本主義世界裡找一個嚹隙,嘗試活出一種自己喜歡的生活模式,為自己的理想活出一種sample,這其實已經很有意義、很重要。」
為什麼選擇務農呢?Rebecca剛開始是想體驗以前服務對象的感受,慢慢發覺自己是真的有興趣。她表示,在香港進入農業的其中一個困難,是很難找到可用合理價錢租用的土地。「許多地主已經移民去了國外,有些人又覺得等政府開發徵地就好。另外一些也想保留土地作耕種的地主,卻同你三唔識七,信任難以建立,租給你都怕到時收不回來。」
Rebecca現在暫時借用朋友的土地來耕種,同時向朋友學習種田。「最近在種韭菜、薑,剛剛種了番茄,還有榨菜等,一邊種一邊觀察學習。」Rebecca說,農業不僅是身體上的辛勞,也要知道許多知識和技能,每一樣作物在怎樣的土地、氣候、環境中能夠生長,已經是很大的學問。要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,左手會握鋤頭,右手要會上網,真是一生也學不完。「一開始也會猶豫,我年紀也不小了,到底捱不捱得住?慢慢又覺得,耕田係辛苦,但是不痛苦呀。」
離開全職工作二年多,Rebecca仍在摸索如何過好她的農業生活。「至少我都未搵到食——不能夠靠農業來維持生計。」經濟上的不安穩,會不會令她有點退卻?「其實我覺得自己是有點不甘心的……我還沒有開始呀!如果是試過了,發現自己能力不夠、天分不足,那ok;但我連自己的地都還沒找到,沒理由這麼快放棄吧!」Rebecca說,之前在工作中認識了大陸的一些返鄉青年和農夫,他們一堅持就是十年,也給了她很大鼓勵。
近年來,香港的農業似乎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。然而,Rebecca觀察到,談論、留意的人是多了,實際參與、用心鑽研的卻未必很多。「反過來,當傳媒集中採訪年輕人甚或一些『文青』的時候,傳統農夫的聲音或許會被忽略。那些老農夫,這麼多年來就是以耕種為生、養大了這麼多個仔女,但是他們不會有空跑出來說,自己多麼喜歡農業。在香港農業的討論之中,很多持份者的意見未被呈現。就像之前做NGO的時候,你和村委會傾,是否能代表所有農民呢?」Rebecca說,很多事情都要從正反兩面甚至多個角度來考量,而這就是她所理解的人類學的精髓:不滿足於表面的繁榮,而是要進一步分析與反思。Rebecca的農業實踐,或許也是一種go native的參與式觀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