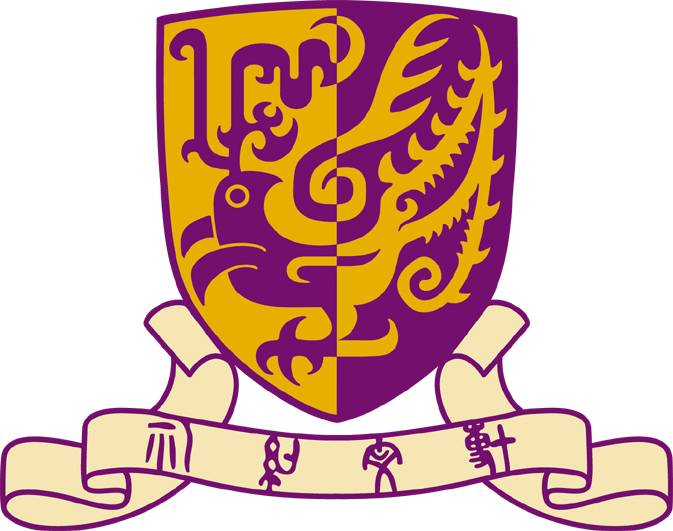「我讀的中學有很多戶外項目,那時就開始覺得,周圍去的自由奔放真的很好、希望之後也能做一些對住大自然多過對住人的事。於是大學的時候,就揀了港大的生態及生物多樣性這一科。日常上堂都要出field,陸地、淡水和海洋,按照不同的棲息地,有相應的實地考察、採樣和實驗,當然和之後讀人類學的fieldwork就很不同了。
「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樹木普查,例如屯門公路要擴建,就去數下有多少棵樹、有幾多棵要移植。之後開始接觸sustainability,去了廢棄化學物處理公司工作,負責安排客戶服務、處理文件、監工。偈油、電池、酸水、貨櫃碼頭的危險化學物、油污堵塞坑渠搞到『爆屎渠』、機器運作中過濾網『嘔泡』……工人們從事回收工作的辛酸,令我當時都覺得很驚奇,原來在香港、在元朗的工業村,有一個這麼辛勞的地方!
「再之後入職諮詢公司,在ESG(Environmental, social, and governance)還是藍海一片的時候入了行。當時所做的一個研究項目,我覺得是人生的轉折點。2013年緬甸開放,外資公司計劃進入緬甸投資,而泰國的緬甸難民營也準備將難民遣返。但有些難民營已經有五六十年歷史,難民第二代一直都在泰國生活,如果去到緬甸,他們能否適應當地的生活呢?我當時所在的諮詢公司,和國際人道機構合作,研究緬甸難民的工作技能和求職需要,是否能符合緬甸公司的需求,是否需要為他們提供職業訓練等等。
「那時很大的感受是,人道的問題,似乎比環保的問題更加根本。例如在難民營,居民要自己燒垃圾來處理廢物,聞到很大的臭味。當下就覺得,在這樣的環境中,難道又可以要求他們要做垃圾分類回收嗎?在訪問之中,看到難民們對回到緬甸的新生活的期盼、閃閃發光的眼神,又很令人感慨於緬甸社會文化、歷史和民族的複雜性,覺得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需要關心和了解。那時候,我開始對人類學感興趣。
「同時,我也去到畢業工作幾年後感到迷茫,需要尋找一下自我的階段啦。完成這個項目之後,我就辭職去了台灣。適逢當時香港有比較多農業議題的討論,發覺自己還是很無知,很想體驗多一些。輾轉去了花蓮,膽粗粗地見到誰就say hi,認識了一位年輕的原住民朋友,他也是一個人出來打拼,分了一部分農田給我合作耕種。體力可以訓練,最辛苦的部分,我覺得是性別問題:身為女性真的很吃虧,很多時不被認真對待。我猜很多人關於台灣的想像可能是比較浪漫的,覺得你去到一定很多人熱情招待你啦,但當你是一個外來者、去到農村、從事農業,牽涉到田、錢、機器、水源、銷路,其中的矛盾是很多的。但也正正是因為這樣,能夠比較深入地了解農村。那種親身體驗,後來回想是幾人類學的。
「畫畫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,我想真的是需要一個出口、記錄一些感受。農村最喜歡就是飲酒,有時拎起支原子筆,在日記簿裡畫一下高粱啊米酒啊的酒樽。有時當日的經歷令我想起某一句電影的對白,就把那個場景畫出來。這樣畫下畫下,就覺得幾有意思。近年有幸和一些NGO合作,出版了兒童情緒管理、家庭關係、自然教育等不同主題的繪本。
「斷斷續續一年半時間,用農夫的曆法來說,經歷了三造米。原本只是想到台灣休息幾個月,之後就讀non-profit management的碩士,重回職業的軌道。但是想想又覺得,讀完之後,大概又是去到一些機構,做一些很執行性的東西,談談申請哪些資金、做些什麼項目。想像畢業之後也是走回這條路,我發覺自己其實不是很有熱情。當時不是很清楚自己可以做些什麼,有一種卡住的感覺。於是就想,既然在這條path找不到一個職位是自己想做的,不如嘗試自己去創造一些職位出來啦?
「台灣的經歷令我發覺,社會的運作、人和人之間的互動,好多時才是問題癥結所在,我自己對此也越來越感興趣。見到中大人類學的MA課程,對於不同學科背景的同學都歡迎,就決定報讀。我是理科背景,一開始要讀那麼多readings,是很痛苦的;唯有記住Prof. Teresa Kuan那句,你永遠都是游過去就可以!怎樣吃不消,也嘗試快速瀏覽一下。大概是半個學期之後,慢慢開始適應這種學習的節奏。
「碩士畢業之後,又嘗試了好些不同的工作。其中一份關於商業可持續性,我負責梳理相關的文獻、撰寫研究框架。商業的項目常常要講宣傳噱頭,發佈的時候要搞什麼活動來吸引人,但其實,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實際措施,才應該是最重要的嘛。我自己坐在那裡看學術論文的時候,在知識上比較能找到安全感。
「另外參與了一個公共藝術的項目,以近似口述歷史的方法,梳理南丫島南面村落的歷史變遷、居民對南丫島的想法和感情,再將這些資料提供給藝術家作為創作的基礎。同事來自社會學、文化研究等不同學科,我就被視為人類學的代表。那我當然會覺得有點心虛啦!畢竟只是讀了一個時間不長的碩士課程,也未曾自己完整做過一個很正統的人類學研究。但我也是硬著頭皮,找居民聊聊天、寫寫田野筆記,想到怎樣做就去試一試。」
「『樹在街頭落淚』,是一個藝術 X 生態學與人類學的跨界創作,圍繞灣仔樹木這個主題,包括『落葉雕刻故事展』,和一系列工作坊、導賞、講座,期望是一個從觀察、體驗到討論與反思的過程。本來我是希望可以通過interview和focus group來收集一些故事、由此來進行樹葉雕刻創作,因為疫情關係,變成以新聞和歷史資料為主。但我依然邀請了王惠玲博士來做有關口述歷史的講座,因為抱著怎樣的心態去聽人說故事、訪問之後如何消化和論述,對於從事藝術或是其他實踐,我認為都很有用。
「『灣仔賞樹地圖』從維園到夏慤道,這一條路線,有很多東西其實可以從很多角度去看,包括樹木。之前讀到人類學家Laura Rival研究亞馬遜雨林Huaorani族的文章,講原住民怎樣去看一棵樹、怎樣去命名,這就和我自己讀ecology的經驗很相關——那時我背植物的拉丁名真的背得很辛苦,不知道為什麼永遠都記不入腦。我開始思考,這些我要去記的名字,對我來說的意義是什麼呢?當我學習到,原來原住民去形容樹木的時候,是和自己的生活經驗相關的,我就嘗試套用在我自己生活的這個urban setting的地方。行過一棵樹,不一定要認得出它是細葉榕還是垂葉榕,但知道它是一位歌手種落的、是末代港督種落的,或者它的形態很美麗,或者有兩棵樹生長得很近而都生活得不錯、這在生態學上是很獨特的現象——於是我把它們命名作『同伴樹』——這些聯繫,我想比較會令大家感知到樹木的存在和其中的歷史。
「『歌聲樹』是美國歌手約翰·丹佛在九十年代在灣仔道種下的,他很出名的那首歌,叫做《Take Me Home, Country Roads》。而盛傳,這裡是張國榮的出生地。我其中一個比較早的作品,是在文華東方酒店的一棵古樹下撿了一片樹葉,雕刻出張國榮的肖像,再帶回到灣仔道拍照,希望藉由這塊葉,將一些精神意義帶回到灣仔。『落葉雕刻故事展』的其他作品也是這樣,結合不同的故事、題材和元素,和自然的物料互動——在展覽中,每個display旁邊會有一張作品剛完成時拍下的照片,而展品本身則是到時樹葉自然萎縮的狀態。最後的那個講座,本來我是真的想做一個爐邊會談,邊講邊將樹葉放到火爐裡燒,表達生命的循環,可惜場地做不到。
「做這個project,我比較會覺得是在分享一個方法。這幾年有很多風向、立場,好像人永遠被社會的大氣氛拖拉著,很多時候,即使身邊好像有很多朋友,仍會感到孤獨。但是,在這個城市裡,你只可以如常生活。要怎樣去處理這種情緒呢?我大膽嘗試用生態學跨人類學,是因為很想去看看,人類和其他物種去互動的時候,所產生出來的情感和行動的變化會是怎樣。如果我要將一些personality加諸其他生物的時候,我覺得樹木是很loyal的,它們永遠都站在這裡,等你去找它們聊天。一開始我present這個project給朋友聽,他們會笑說:『哎呀又是抱樹、攬住棵樹那些呀?』或許他們覺得科學就是理性的科學,情感是不相關的東西。然而,當你嘗試去觀察,開始看一看樹皮、認得出樹木的時候,就會在意它的存在,感覺和它在溝通。不是說去看樹即刻就會開解到你、即刻會令你心曠神怡,不是那麼神奇啦;但是認知到世上有無窮無盡的事物可以發掘,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令枯燥日常變得有趣味,所帶來的心境的變化、壓力的舒緩,於我是真實的體驗。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project分享這樣的一個觀點,,不是說服大家去執樹葉,也不是推廣樹葉雕刻、把它塑造為很靚的藝術品,只是當你漫步在街頭,尤其有時心情悶、覺得自己困在原地的時候,經過每天都會經過的樹木,嘗試留意一下它的葉落花開,思考所有生命每分每秒都在變化中,對於個人的心態調整,可能會有所幫助。
「從構思到籌備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,第一次做個展;『個展』在藝術界似乎是很大件事、應該很厲害,但我不太感受得到,覺得是one-man band去砌一些東西出來比較多。因此有點壓力,擔心自己的能力或想法未必做到藝術界的標準。然後,我想起在南丫島做人類學研究的經驗,也是自己想到怎樣做就怎樣做,可能開創自己的方法就是我存在的意義。這樣想我就有點釋懷了,到時出來的效果是怎樣就怎樣吧!
「這幾天,我有個感覺是,這幾年來,即使在很多社會壓力之下,也有一些東西是在變好的:個人的韌性和創造力變高了。而我想這是值得大家去celebrate的。可能在很多很實際的人眼中,我做這個展覽會達到什麼impact呢?會令到大家即刻愛地球愛樹木嗎?不會啊。但是,我是覺得,要相信運用自己的創造力去做到一些東西的時候,總會吸引到一些人的回應。這個心境,對於處世,我覺得都好緊要。」
【樹在街頭落淚】www.wanchaitrees.com
Instagram @7eresa_storytell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