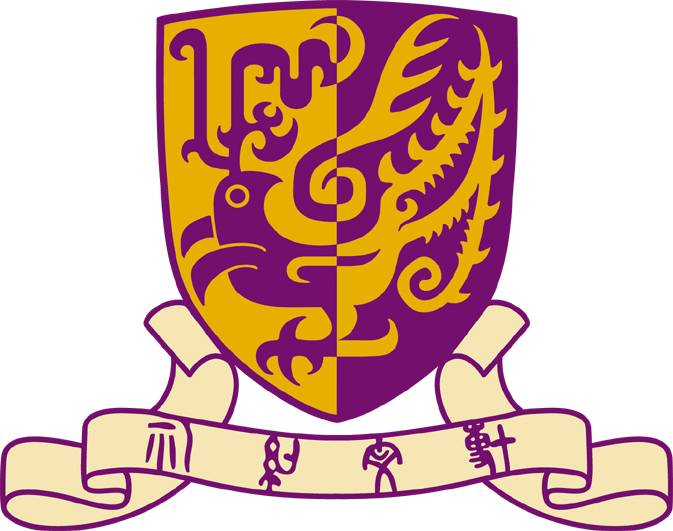「一畢業,我從事的工作就是和出版相關的,是做發行。當時其實是有得揀的:要麼做很能賺錢的工作,例如銷售或者金融行業,我都有見過、有些都進入了second round;要麼就是選很有理想的工作。而我想著想著,始終還是想出書,完成中學到大學的心願。所以我就去了做出版,認識一下人、學習一下怎樣做。」於是,從人類學系碩士畢業不到一年,徐焯賢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說《天王逆子》。「當時不記得是哪一位同事和我說,『沒人幫你出版不緊要,其實你可以出啊!』我想,對喔,然後我就成立了自己第一間出版社,所有事情一腳踢,很快出了第一本書。」
從中四開始,徐焯賢已經對寫作很有興趣。歷年來,他創作了一系列奇幻和科幻題材的小說,「人類學的想像力」也許在其中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。徐焯賢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曲藝社,其後他寫了《神功戲殺人事件》,在偵探推理中糅合傳統文化知識。「人類學在我寫作中的角色,其實是很難說的,因為整個人的思考方式都不同了、深入到腦子裡,對於佈局謀篇、遣詞造句都有影響。」他笑言,讀了六年人類學不會是白過的。
文學以外,徐焯賢對於文化也很關注。「我也想做一些事情令到社會變得更好——什麼才叫做『好』可能很難定義,能夠更加多元化、將模糊的事情釐清,大概是我所謂的好。」近來徐焯賢為多元文化行動計劃編輯出版了《我們在慶祝甚麼?香港的多元文化節慶》和《Iconic媽媽廚房:跨文化香港滋味》兩本書。談到出版過程,徐焯賢說,也有不少困難。「這兩本書都是由多位作者合寫而成,有很多事情要不斷多方來回溝通,才能整合成一本書。」談到這裡,徐焯賢舉了自己最新出版的小說《我摔倒了我的幸福》為例。「這本書是我和另一位作者合寫的。一開始我們以為兩個人一起寫,一人只需要寫半本,會比較容易,怎麼知道原來正正相反——一人一半的原定字數不夠我們寫,後來整本書從六萬字變八萬字,都還不夠。而且我們想要合作得特別一點,一個寫男一個寫女,一個從1997寫到2017,另一個則調轉,從2017寫到1997。每人一章,事情會重複出現,要怎樣才會重複得比較好看呢?我們又設定,兩個主角,一個可以看到未來的東西,另一個可以看到過去發生的事情。」徐焯賢自嘲,這樣複雜的合作方式,要做到嚴絲合縫,簡直是攞苦嚟辛,「但是我們又覺得非常之好玩囉。」
徐焯賢說,本科畢業後升讀碩士,是想嘗試學術的道路,後來發現並不那麼適合自己。「我覺得鍾意一樣嘢就要百分百投入,但我在做研究、寫論文的時候發現自己沒法二十四小時都想著這件事,所以還是試試做別的吧!」編輯出版是勞心又勞力的工作,從內容、文字到格式、印刷,功夫很多。徐焯賢常常從白天校稿到凌晨,「看到眼都盲,你想不到會那麼辛苦!而且一本書有很多零零碎碎的東西,總會有細節出問題,只看你能不能醒覺、發現,在付印前及時補救,但總是會有遺漏。有做過出版的人都知道,唯有下次再做好一點。」投身出版業多年,徐焯賢認為現時的挑戰,在於競爭不只限於出版行業內,所有與娛樂、知識相關的文化產品,都可能是你的競爭對手。「網絡技術尤其令到資訊的傳播和接收變快、變直接,這影響到大眾的閱讀口味,使得其他媒體都要跟上這個節奏。出版這個行業需要有一場大革命,這個行業必須想出一個新的發展方向——這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事,要大家一起思考。」
對於有意入行的年輕人,徐焯賢說,「出版這個行業其實很大,雜誌、書籍、出版社又得,freelance做出版當中的某一個部分又得,有很多不同參與的方式。」而關於行業發展前景,他就覺得,社會發展的需要可以前瞻,但是否百分百準確就很難說。「香港常常覺得讀書是職業先修,我覺得這是錯的;讀書其實是訓練你的大腦,令你看多點、想闊點,接觸的知識層面多樣一些。現在香港的樓價那麼高、生活壓力那麼大,也許真的不是可以追求理想的年代,這不能怪責年輕人,是整個社會氛圍的問題。但其實很多東西是猜不到的,譬如說,我讀書的那個年代,小說依然很流行、報紙依然很多小說連載專欄,我是看著這些專欄一個一個cut的;到了現在,有些出版社甚至不願意出版小說,說沒有銷路。這在十多二十年前又有誰能想到呢?反過來,一本小說今年出不了,或許明年有不同的文化風潮,又有人喜歡看呢?如果你覺得那件事有價值,不如你去做推動的那一個。」徐焯賢認為,在香港,只要願意花心機,無論做什麼工作,即使不能大魚大肉,也不難覓得溫飽、過上自己的生活。「想得簡單一點,再過幾十年,可能我已經不在,可是你到圖書館看,有我的名字在、有人類學在,這就已經有其價值。」
(照片鳴謝: 程啟榕)